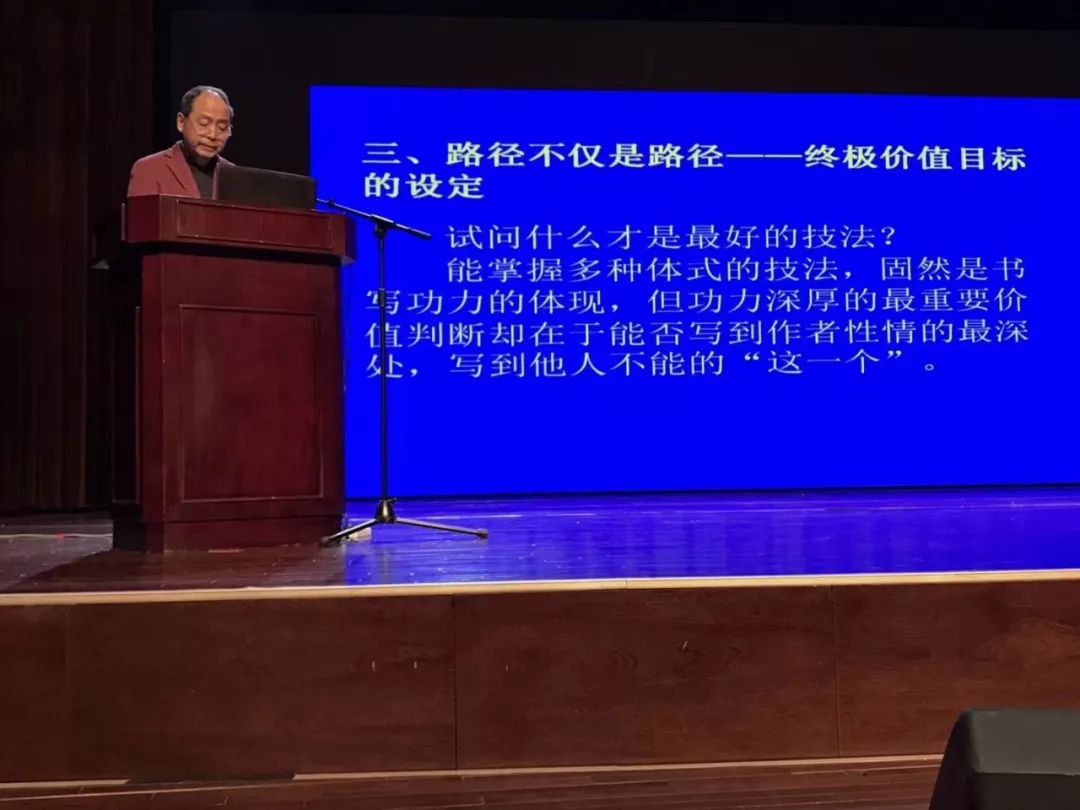书法实践的终极价值追求
——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批评展乌海论坛演讲稿
/ 鲍贤伦
中国当代书法实践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书写技法的基准水平明显提高。这无疑与以下一些因素紧密相关:全国与地方各级书法团体的建立以及由他们组织了许许多多的书法展览;数百个书法专业院系(同时专、本、硕、博体系化)以及成千上万个书法培训机构组成了规模庞大的教学阵势;出版、印刷技术和网络提供了史无前例的高质量图像和视频资料;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组织的“国宝展”和各大拍卖行组织的古代书画拍卖让人们比较方便地直面古代作品……。这些条件都是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它直接导致了书法人口的众多与书写技法水平的提高。在一般的社会语境中,“书法”一词近似于“书写技法”。比如:在教学中,技法是当然的重点,书写示范及其视频最受欢迎;参展的作者千方百计想表现自己的技法水平,评审的专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别无选择地以技法高低为取舍依据;一些在展览中脱颖而出的获奖作者,在“成名作”之后产生严重的路径困惑,甚至每况日下。这让我们看到只有技法的“一家坐大”并不利于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中国书协在其主办的展览评审中增加“审字读文”环节,多少是对“裸露的技法”现象的补救。
技法对书法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它既是作品的基本要素,也是书家长年累月千锤百炼获得的功力体现,无论从全局上说还是从个别上说,我们都还不具备轻视技法的资格。但是,书法不仅需要技法,还需要其它。古人将其归纳为两类——功力与性情。所谓“学书在法,其妙在人。”此处以“人”与“法”对言,即如以“性情”与“功力”对言。所谓人的性情其实就是作者的修养,是作者的才调、风度、人格气象在作品中的生发。我们不妨借用“性情”一词来总括人的学养、审美判断、生活态度、生命质量等等。正是“性情”与“技法”一起构成了书法艺术实践最重要的两块基石。技法不能替代性情,性情也不能替代技法,但是性情可能会“选择”技法。因为性情会影响审美倾向,进而选择符合审美倾向的那部分技法。性情当然是主体的,技法看似客体的,其实所有真实发生的技法都是作者性情筛选过的保留痕迹。技法与性情本来是一体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是到了当代才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性情被忽略,剩下跛脚的技法,如何走远攀高?
古代书法的主体是文人士大夫,他们首先是发表文学作品,不经意间却成就了书法精品(如《兰亭序》、《祭经稿》、《黄州寒食诗》)。当现代汉语替代了古代汉语、白话文替代了文言文,也给了“文书一体”的书法传统致命的一击。从此,书法作者是为了要创作书法作品,才去古典文库寻找一件文学作品。当代展厅容量巨大的空间又再一次雪上加霜般改变着阅读赏玩的千年旧习。“文书分离”后的书法创作,写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大体量、空间感、取悦感官,成为在竞争性展示中的制胜法宝。“文书分离”既疏离了文,也就必然一步步地疏离了人。人的“性情”渐渐被“空置”。
性情有先天的,有后天的。我们无法选择“与生俱来”的那部分性情,但后天的自我养育很重要。比如通过文史哲的学习和为人处事的实践来涵养自己的心性。中国词汇多有讲究:艺术——艺在先,术在后;文艺——文在先,艺在后。书法的繁荣光在技法上发力是难以真正奏效的,人的丰富性才是艺术多样化的内在依据。
以上所言皆为书法实践的路径问题,但路径不仅是路径,它直通书法实践的终极价值目标,即一个书家的最终理想是什么,理清并确认理想的彼岸,路径问题自然不辩自明了。在漫漫的书法实践路途中,技法功力由浅而深,性情修养由贫瘠而充盈,两者相伴而行,唇齿相依,共同生长,这是愿境。性情离了技法便无处落脚,而技法离了性情也不可能“一家坐大”。试问什么才是最好的技法?能掌握多种体式的技法,固然是书写功力的体现,但功力深厚的最重要的价值判断却在于能否写到作者性情的最深处,写到他人不能的“这一个”。一个书家要主动进行多样化的书写试验,但根本目标仍是寻找与自己性情最契合的笔墨方式,而不是叠加多多益善的技术能力。一个书家可以也应该自觉地把技法训练与性情养育同步同频起来,一旦“寻找”(这里的“寻找”意味深长)到最个别的性情以及与此相应的最个别的书写方式,那就是书家的大幸事了。这样的书家多一点点,书法艺术表现人性的丰富这一命题也就功德圆满了。
这既符合“书如其人”的古训,更着意强调当代人本立场,以纠当下书法实践之偏,并企望在人与书法的互相成全中完成文化的人文意义。
2018年9月12日于杭州